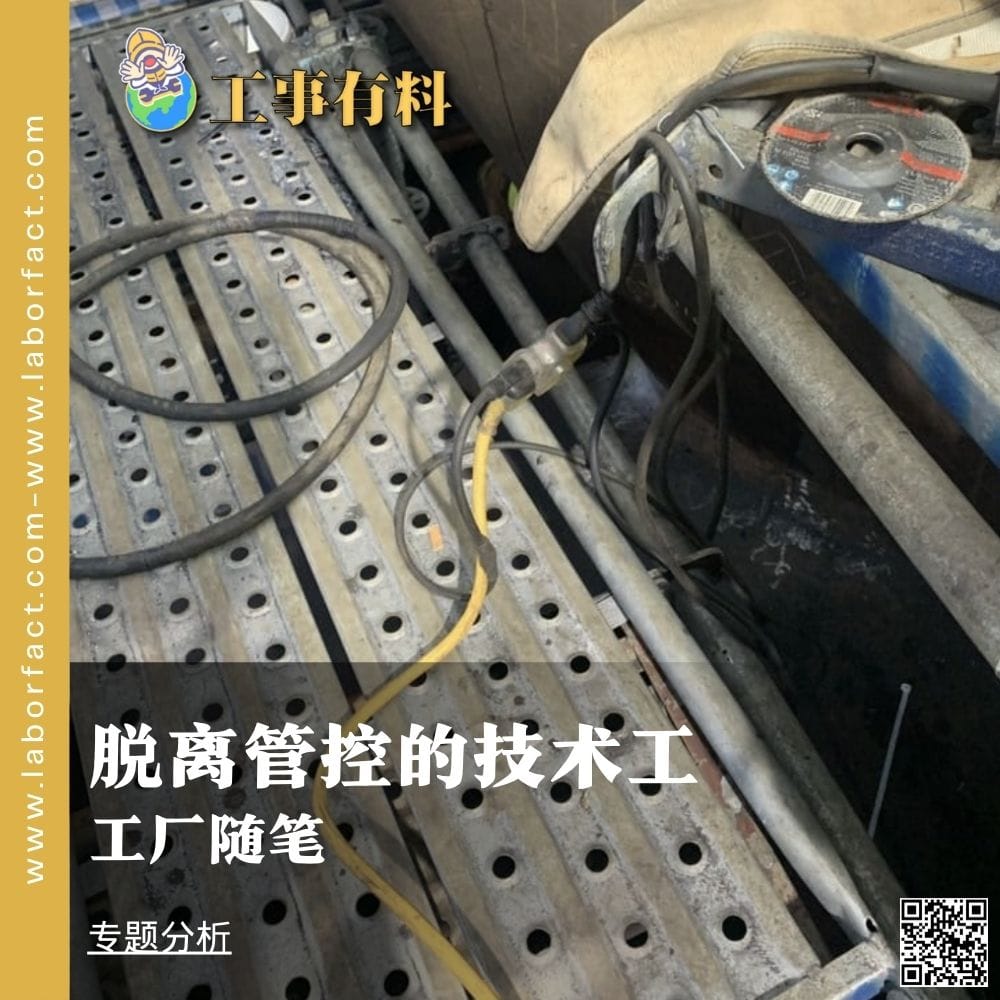【读者来稿】工厂随笔:脱离管控的技术工
来源网站:www.laborfact.com
作者:
主题分类:劳动者处境
内容类型:深度报道或非虚构写作
关键词:技术工, 工厂, 现场, 领班, 过程, 帆布
涉及行业:制造业
涉及职业:蓝领受雇者
地点: 无
相关议题:肮脏或危险的工作环境
- 工厂位于海边,恶劣的气候条件使得工人们在大风大雨中工作,经常面临积水和设备浸水的困难环境。
- 焊工作为技术工种,在生产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他们的工作环境复杂,需要在高空和恶劣气候中完成任务。
- 外籍劳工在工厂中占据大多数,他们中的技术工种如焊工,虽然工资较高,但面临的劳动条件和管理挑战更为严峻。
- 焊工通过在工作区域搭建帆布等方式创造出自己的工作和休息空间,这种做法虽然为他们提供了一定的自主性,但也反映了监督和管理的缺失。
- 领班和管理人员在监督工人时面临困难,由于工人数量众多且分布广泛,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变得复杂,导致工人权益保护存在盲点。
以上摘要由系统自动生成,仅供参考,若要使用需对照原文确认。
编按:重工业给人的印象常常是庞大的钢铁巨兽,所有人在其面前都显得渺小。但真实世界中的重工业工厂是什么样子?这篇读者投书着重的不是工人们的辛酸,而是现场的劳动、制造与监督过程:风雨不断的厂房、高空的焊接作业、工人们在控制与自由之间游走的微妙状态。这篇文章描述了工人们如何在恶劣环境下寻找喘息空间,也呈现了焊工与管理者之间复杂的互动与权力平衡。
注:出于安全考虑,虽然这篇工厂随笔涉及的经验和想法都是真实的,但工厂具体所在地点、产品等方面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虚构。我试图在不影响文章内容有效性的情况下,尽可能避免暴露工厂所在地点。
一、工厂背景:海港边的重工业
工厂位于一处大型海港。工厂所在地本身也是填海造陆而成的新生地。建在这种特殊地点的原因与土地价格较无关,而是因为这间工厂所生产的产品是大型钢铁结构,主要用于海上钻井平台等大型基础设施。位于海港,对工厂运输产品来说是优势,但对于生产过程来说却有诸多不便。冬季的海边风大、雨多,附近城市感受到的普通降雨,在此处可能会导致大量降水灌入工厂,甚至让工作无法继续。因为工厂本身生产大型钢铁结构,这些产品的长宽高都以数十米为基础起跳。这意味着工厂内也需要有庞大的空间来容纳产品,还要预留吊挂、翻转的空间。所以,这间工厂的结构也并非一般制造业工厂的厂房规模,而更像是造船厂的棚屋结构。普通厂房高约40米,特殊位置高达70米以上,四个方向中只有东西面建了完整墙壁,为了方便运输,南北面并未建任何墙壁或挡风雨的结构。也因此,只要风向是偏南北,同时又下大雨,雨水会直接灌入工厂内,导致地面残留大量积水。电线、气瓶、机器等泡在水中,这样的情况已是常态。这间公司内,共有5间类似规模的厂房和一些特殊的附带设施(例如喷砂、喷漆厂等),为了将产品运至外海,工厂只能位于这种特殊地理环境中。同时,考虑到运载船只的吨位、吃水深度,也并非所有海边土地都适合建造此类工厂,只有大型邮轮停靠的商业港口具备这种条件。
每间厂房都可以容纳200-300人同时工作。但因为工程进度关系,每间厂房都并不会完全处于生产状态,通常每间厂房有150人左右同时进行工作。
工厂内主要有两类员工,办公室员工和现场员工。办公室员工主要是设计、财务、人资、公司高层等,他们主要在工厂旁边有一栋专门的精致小巧(相较于工厂的大型规模)的总部楼内工作,除了吃饭时间外,与现场员工交集不大。而现场员工包括了制造管理、质检、电焊、组装、量测等部门,他们中有基层工人也有管理层或专门技术人员。办公地点要么直接位于厂房内,要么位于厂房内的独立办公室。这类办公室是在厂房角落搭建的平板屋,通常比较简陋,与仓库混合使用,但也配有空调、白板、电脑,方便现场沟通协作。
现场人员除了分工、部门的差异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差异——国籍。这间工厂雇佣了大量来自东南亚的外籍电焊工、组装工、清洁工等现场施工人员。比例上,本地工人所占比例不足十分之一,绝大多数完成一线工作的工人都是外籍劳工。而这些外籍劳工当中,内部自然也存在差异,有牌照的电焊工工资最高,而电焊工的领班是工资最高的工种,甚至超过不少坐办公室的本地劳工。而组装工、清洁工等技术性较低、缺乏门槛的工作,则只能领到最低工资。与此相对,本地员工即使在现场也大多不从事体力劳动,而是进行进度管理、监督工程进度、协调质检或操作特殊机器(例如吊车、重型运载车等)。另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工作者,是具有大学学历的东南亚籍工作者,在工厂内担任翻译、测量工程师。他们通常薪资更高、也有更多升职机会。
二、制造过程
在电子厂或者一些轻工业的劳动现场,生产通常是以机器或生产步骤为核心组织起来的,通俗来讲就是流水线。产品从一个机器进入另一个机器,从一个工序进入下一个工序,并不断完成组装,变得更加完整。但在这种重工业场所,所有工序和机器以及工人都是配合产品进行移动的。在非必要情况下,产品本身不会进行移动。叉车、高空车、吊车以及组装工、焊工都随时围绕在产品附近,一点点将其完善。
粗略来看,制造过程分为这么几个过程:原料就位、组装、打磨、点焊、测量、甲方验收、焊接、打磨、质检、测量、甲方验收、喷砂涂装。因为钢铁结构本身过于庞大,通常整个组装、焊接过程需要3、4个大型步骤才可以完工,这个制造过程也会重复3、4次。在过程中,客户最在意的是整个结构是否歪曲,所以要进行多次测量,也在意结构是否稳固,所以会针对焊接位置进行质检。一旦测量或质检发生不合格。那么工人只能切掉或铲掉已经做好的部分,重新组装、焊接。很多时候,这种生产过程的难度并不在于速度或整个过程有多少技术难度要克服,而是在组装、焊接过程中的品质稳定性,因为出现瑕疵意味着工期要递延,后续步骤都会受到影响。焊接又是最容易出现瑕疵、考验工人技能,并且无法自动化的工序,所以优秀的焊工是工程能顺利推进的前提。
虽然上述制造过程有几个清晰的名称和顺序,但在实际加工过程中,它又是相互交叠错位的。因为产品本身是3D立体结构,这意味着底层可能已经进入焊接、打磨步骤,上层才刚刚开始进行组装。而各个步骤又会涉及机器、工人、脚手架的空间位置摆放,后续步骤也可能影响之前的步骤。在现场,如何协调有限的空间、机器资源和不同工种,顺利达成工作的持续推进,这是现场管理人员面临的最大挑战。在工作现场,除了“安全第一”这种被喊到麻木的口号外,“合作、协调”是最常出现的字眼。
工人会拜托领班帮忙协调事情,领班也会拜托更上级去协调。有时只是拜托其他工人暂时停工,也有时会涉及从其他单位借用吊车、叉车来完成任务。我也经常听到主管被询问,是否可以借用一些焊工来协助完成其他单位的任务,但这种请求多半会以“人力不足”为原因而回绝。即使现场可能真的存在空缺人力。但从单位内部的视角中,处在待命状态的工人可以随时配合现场需要进行赶工或协助特殊事项,而调查现场工作空缺以及从其他单位要回工人,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借用机器车辆都很好讨论,但借用人力在现场是最困难的。
三、焊工:脱离管控的技术工
正如前文所说,有经验的、技术好、熟悉现场并具备一定协调能力的焊工,是这间公司能稳定运作、按时交货的基础。而焊工也是现场最难管控的技术工。这种难以管控一方面是因为其角色之重要,另一方面也与生产中的空间安排有关。
产品是大型海上钢铁结构,所以其尺寸规模必然远大于人体和现场各类车辆机器。这意味着工人们需要使用脚手架抵达每个施工位置。这样的生产形式,相较于制造业,更接近建筑业的生产方式。而焊工抵达生产位置,也就是钢铁结构件的连接处/焊缝之后,还需要在现场进行前置作业,包括拉来焊机、气瓶、挂上帆布、安装预热片、预热机等等。其中,安装帆布是因为工厂位于海边。强烈的海风带来温湿度剧烈变化,这会造成焊接品质下降。帆布是这种恶劣气候条件的应对措施。
但帆布挡住了海风,同样也挡住了监督的视线。随着生产继续,焊工并不会即时清理掉之前所挂上的帆布,而是会在临近位置继续叠床架屋般地安装帆布。在一些特殊的高空作业位置。焊工还会为自己的休憩处或方便处额外多挂一些帆布,将原本连通的空间切割成各种功能区块。这些帆布方便了焊工工作,也保障了他们工作过程中的休息空间。但相对应地,领班或本地监督人员从外面看来,就只能看见一个个迎风飘扬的小帐篷,而无法看见其中工人的状态。
一个应对的方式是,安排领班进行查岗。但这种做法并无法有效控制工人的劳动过程。一方面,领班人数相较于焊工人数仍然是少数。大约20位焊工对应一位领班。领班若要巡查所有工作岗位,则需要钻入每个帆布、爬上每处脚手架,而每个焊接位置也大约只有1-2名焊工。这意味着即使领班经验丰富、很熟悉现场状况,要巡查一遍所有工位,大约也要花费1小时以上的时间。而领班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完成(进行前置、清收、处理各种现场临时状况),现实来讲,每半天能巡查一次已经是极限了。而另一方面,大部分领班也不会进行这样的动作。即使看到工人在休息,并未连续处在高强度工作中,或甚至工人在角落抽烟玩手机,他们也只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仰赖工人的配合,才能完成自己的工作,得罪基层工人也不一定会获得本地管理人员的赞赏,更有可能让自己彻底失去信任,在未来工作中处处遇到障碍。而且他们也知道,对于焊工来说,此地的工资并不若欧美那般高昂,并不值得为了这样的工作费尽心力,累死累活。
所以,依靠外籍领班进行生产监督,只能达成最基础的分工效果,并无法真正控制工人的劳动过程。有时,某些工人的当日分工其实只需要2-3小时就可以完成,但工人处在空缺状态,也难以被投入下一个工作过程中,因为现场无人可以也无人有意愿去紧密安排这样的生产过程。而承受业绩和进度压力的本地现场管理人员呢?他们大多处在两难之中,一方面,他们希望最大程度利用人力,来尽快完成进度,不然就会遭到上级办公室人员的责难。另一方面,他们也担心这样的催促会破坏自己与外籍领班之间的关系。过往,曾经因为类似的工程进度催促和一些惩罚性措施(例如禁止特定工人加班)而造成外籍领班和工人一起罢工。他们宁愿被上级责骂,也不愿因此而对下级过分施压而惹出更大的麻烦。所以在工作过程中,本地现场管理人员可能并不认识几个基层工人,但他们与外籍领班之间具有密切的协作关系。一些现场任务(例如查看质检结果)会被交由外籍领班去完成,他们也会尽可能提供资源去协助外籍领班的工作(例如借用车辆、争取更多施工时间等)。这些本地籍的现场管理人员,即使没有相关教育背景,也都会使用工程英文甚至东南亚语言与领班进行沟通。这样的关系结构,形成了一种屏障,阻碍了上层的工期压力和控制欲望传导至焊工。而相对的,现场基层管理人员和外籍领班就常被上级视为工期延误的罪魁祸首,承受最大压力。
在我最熟悉的四位外籍领班中,最愿意配合、工作最认真的一位,曾经就因为这样的压力而过劳病倒,请假2天无法工作。而那2天,也是现场生产最混乱、最接近崩溃的时间。第3天的时候,虽然仍感到头晕,但他还是回到了工作现场。而本地现场管理人员们,面对这样的压力,则更可能以辞职来面对。我的主管曾多次表示“公司上层活在幻想中”、“这个公司有毒”、“这个公司的人力政策有问题”,甚至还有管理人员主动向上级申请要下放成为普通工人,不愿意牺牲假日来应付繁重的工作。也许,增加现场管理人力和外籍领班数量,可以某种程度化解压力,并更精细调控焊工的工作安排并进行回馈。但这样的方法势必增加公司成本,又是上级不可能采取的。而即使这样的调整真的能达成,焊工也未必会认真乖乖接受自己被控制的事实。他们仍然有最后的杀手锏——罢工——来应对所有的系统性惩罚和控制。焊工们同吃、同住又在生产现场建立了自己的主导权,当个别焊工被惩罚或解约,其他人不会愿意出头协助。但如果面对系统的变化,例如加班时数减少,工作量普遍增加,他们会迅速反应、团结在一起。而这是现有的管理控制方式所无法克服的。
另一种来自上层的管理方式也可能干预焊工的劳动过程。公司会要求基层管理人员回报所有焊工的分工,并统计每位焊工的工作瑕疵率。瑕疵率高于5%的焊工会被定期列出名单检讨,并以禁止加班/削减工资作为惩罚。但在实际操作中,这样的名单并不会被直接执行。基层管理人员有最终的决定权。因为现场经常工期延误,确实需要大量的焊工投入生产,不让焊工加班等于增加管理人员的工作压力和难度。所以这些名单中,除了少数人之外,大部分人最后都会被免除惩罚。被惩罚的人多半也在工作场所中与其他焊工和领班关系普通,无人愿意为他们说话。主管曾经跟我说过,他们本来希望这样的名单可以是一份奖励名单,对完成特定困难任务并且品质较好的焊工给予奖励金,来鼓励大家从事较难的任务,并激发生产积极性。但这样的奖励金制度并未被高层同意。
公司核心生产过程仰赖的是脱离管控的技术工,这让公司高层长期感到不满。所以,他们最新的对策是,打算将现场工作外包给多家承包商,与承包商直接约定工程期限和报酬。一旦承包商违约,则可以直接对承包商罚款。这种外包模式即将被正式应用,但在焊接部分恐怕面临无法找到承包商的困境。因为熟悉相关工作的人都不敢承接如此具风险的任务。而如果真的成功执行。现场工作将会很接近建筑业的分包模式,相应劳资问题会更复杂。
四、加班是一种奖励
常听人说,在制造业加班是一种奖励,或至少,并不是一件坏事。在这间工厂中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风气。在我上班的第一天,主管现场的厂长就说今晚我可以留下来加班,要把加班时数尽量用满,把加班费尽量拿走。而公司内部,办公室人员不太容易申请到加班费,但对于现场人员来说,加班申请几乎可以百分之百获得批准。似乎有这样一种意识在背地里发挥作用“现场工作是辛苦的,是与工资不相称的”,所以我们需要尽可能利用加班制度来获得合理的报酬。而对于公司上层,现场人员的加班似乎也要被充分给予尊重,因为他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现场进度延误,现场人员的加班,不仅是一种顺服的表现,也是对于工作投入的表演。
在加班时间内,到底是不是真的在完成工作任务。这也是一个模糊的状况。有的工作确实有可能在8小时内完全做完,但它意味着精神的高度集中和身体疲乏。而不加班也意味着工资的减少。但如果把同样内容的工作以一定间隙进行安排,平铺至11-12小时中,则不会显得过于紧凑和压力。既拿到了加班费也减轻了自己的工作负担。不过无论选择哪一种工作方式,现场的繁重工作都意味着工人回到家中后,并没有足够的余裕进行其他活动来休闲,只能被动地用滑短视频、吃饭来填补休息时间。日复一日,生活中其他空间被压缩减少,也更让人没有欲望去争取下班时间。因为下班后能去哪里呢?几乎也没有哪里可以去。对于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和中年无家庭负担的劳动者来说,这种生活方式或许还可以接受。但对于30多岁结婚成家的员工,家庭、子女关系与工作的冲突最为严重,他们在工作中耗尽心力,缺乏更多耐心面对子女和家人,自己的生活随时处在崩溃边缘,也是不少人最终离职的原因。
对于外籍劳工,加班则是他们中一些人选择来此的原因,因为本国经济不景气,缺乏工作机会,或者即使仍然有工作但也会被强制休假减薪。他们来到异乡本就是为了尽可能多争取赚钱机会。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加班更是一种天然的奖励。在此地的生活中,他们除了工友之外几乎没有更多认识的人,也没有一种过本地日常生活的企图。再加上偏远的工厂和宿舍因素,如果提早下班,他们面对的只有宿舍中的无聊时光。于是,争取更多的加班时间,宁愿在工作现场打发时间也不愿回到宿舍中,成为普遍共识。我问过一些外籍工人为何选择来此打工,大多都觉得此地工资并不算高,但好在可以加班以及工作本身强度不大。所以即使在欧洲或中东,他们可能能获得更高的工资,但他们仍然选择来到这里。对于外籍劳工来说,工作与生活也存在一种平衡,那是在工作间隙中寻找休息、主导权的平衡,是获得加班费与适当工作强度之间的平衡。
五、海风下、噪音旁:焊工的劳动环境
前文里,我谈到了焊工在现场的劳动强度和连续性难以被工厂控制。这似乎让人以为,焊工在这里的工作是相对轻松的、自由的,但现实情况比这更复杂。说是自由和轻松,这一点确实也得到许多工人的同意。我经常在工作间隙随机与遇到的焊工聊天,他们大多认为这里的工作相对轻松、舒服,可以有一些休息时间,也不会被催得太紧。但这种轻松和自由是一种相对概念,说起强度更大的劳动环境,他们会说起自己在中东打工的经历,在那里他们会被工头盯着干活,不能有一丝懈怠,而工作场所是有人端着枪监督工人劳动的。在此地的劳动强度是相对于这种严苛奴隶式的工作模式的“轻松”,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轻松与舒适。
焊工的疲惫也不完全来自于劳动强度,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劳动环境。这也是所有基层蓝领工人的状况。要知道,即使是坐着休息,在一个有空调、软垫座椅的办公室休息,和在一个满是噪音、可能身处高空、周边都是钢铁结构、随时有安全风险的地方休息,两者对于身心的恢复程度有天壤之别。更何况众所周知的,焊接这种劳动技术必然伴随着高温、强光、噪音与粉尘空气危害,焊工在劳动时除了身体本身的消耗外,周边环境带来的伤害也占据主要部分。
因为这类钢铁需要安置在海上,所以通常都非常庞大(以陆地尺寸来说)。我曾在组装后段工程处登上大约35米高处的一个焊接平台,当时是为了近距离了解现场的一些技术用语,但更令我震撼的是空中工作的环境。本身登上工作平台的路程就很曲折,在厂房坐电梯登上30米高处,然后穿过堆放各种焊接、打磨设备和帆布的空中走廊,再爬上多个临时的脚手架,最后挤进一处仅容纳半个人身体大小的入口。进入后,整个平台像是一个铁笼,由几根钢索悬挂在结构下方,包装帆布后看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室内”空间,但其实只是临时的悬吊。而焊工们一天的工作、吃喝拉撒也都在这样的铁笼上完成。铁笼本身是为了符合焊接需求而建造,不会把工人的身体当作优先事项,所以高度仅约1.5米,远低于正常人身高,而且范围逼仄,仅比焊接位置大一圈。焊工在铁笼中的工作需要弯曲身体,在受限空间下完成。而即使焊工处在待命或休息状态,铁笼中也没有休息空间。不说座椅这种基本需求。连稍微远离焊接位置能够减小些噪音的空间都不存在。焊工们大多自己搬铁桶到铁笼中当作休息座椅,也有焊工直接蹲坐或在铁笼地面上多盖几层帆布席地而坐休息。至于噪音问题,只能透过戴耳塞来解决,空中根本没有躲藏噪音的位置可用。而公司所发的耳塞也只是普通的橡胶耳塞,并不是专门保护耳罩,其防护效果也只能说聊胜于无。我在空中待了大约30分钟,尝试与工人了解一些工作术语和他们的状况。等到下来回到办公室,整个人的身体疲惫度却相当于工作了一下午。在交流中,我还发现焊工们除了领班以外几乎都没有佩戴安全绳,工人们的说法是公司以安全绳不够为理由暂缓了发放,他们已经申请却没有得到回音。作为基础安全设备,如果安全绳不够,工程根本不应该开始。这个理由肯定只是公司的借口。根本原因无非是,甲方不会上到这种高空平台来检查,而公司也不愿意多花成本在这种主要用来应付检查的安全装备上。
还有另外一区,这区域直接临近大海,是装卸产品的码头。本来,所有完工的产品才会聚集在此处等待装船,本不应有工人在此继续焊接。但是因为过程中不断有瑕疵未来得及修补,许多工作被留到最后再进行。工人也只能乘坐高空吊笼装置进到这些表面看起来已经几乎完工的大型钢铁巨兽上做最后的修缮。这个区域我并未直接上去过,也是因为安全风险而被主管拦下。但我见过不少焊工从上面下来后回到办公室取暖,那冻的浑身发抖的样子也反映出其中劳动环境的可怕:海风直接灌入身体、两旁看下去要么是水泥地面,要么是一望无际的大海,一阵强风吹过,临时的悬挂设备都会随着身体而颤抖。一整天12小时工作,都无法来到陆地上休息,午餐晚餐只能吃拿过来时已经冷却的盒饭。
虽然焊工是绝对的技术工,也是这间工厂能够运行的依据。他们也的确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公司的掌控,处在一种自己可以安排工作进度和休息状态的自由中。但焊工们的身体仍然需要密切配合工程的进行。工程本身恶劣的环境因素、人为因素(例如赶工)也时时刻刻摧残着焊工们的身体状态。如果说公司在对于工作强度的安排上有所放松,倒不如说是因为本身恶劣的外在工作要素以及相对较低的薪水,让工人们愿意以较低的工作控制和劳动强度来换取这些相对不利的条件。如果这种默契与平衡被打破,那么工人们则直接以罢工作为回应。
工人有事,我们报道
我们收集一线工人的声音,呈现不被主流媒体看到的劳动者生活;我们探究政治经济背景下的劳动体制、剥削逻辑,力求呈现劳动者的处境,看见来自工人的行动和抵抗。快手、抖音等工人使用的社交媒体是我们的主要信息来源。采访劳动者、与工人建立连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希望通过文章和报道的连接,能使所有劳动者团结为一张巨网。我们分析工人受苦的原因,分享工人斗争的经验。工人的声音需要被听到,工人的声音最有力量!
劳动者筑起一砖一瓦,在一条条产线上铸造中国制造的奇迹。劳动本应该被尊重,现实中,劳动者被剥削、被边缘化,主流话语一边将劳动者塑造为卑微、值得同情的受害者,一边忽视、贬抑、打压劳动者的行动。我们希望在劳动者的世界中,重新看见劳动的价值,重建劳动者的尊严。
征集伙伴
如果你也对工人议题、劳动报道或工人运动有兴趣,想参与工事有料,欢迎直接写信联系我们: [email protected] !